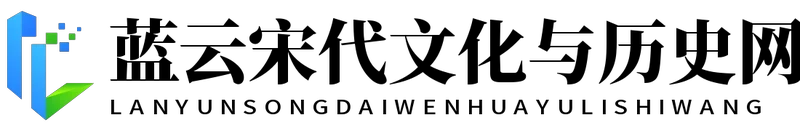从冷兵器时代的集中兵力到热兵器时代的集中火力,从机械化战争时代的合同作战到信息化战争时代的联合作战,每一种战争形态都孕育出新的作战理论。如果仅仅将这些作战理论视为战斗经验的总结和升华,那么人们很难从中窥测未来新的战争形态将孕育出哪些新的思想、新的理论。为此,本文从边际成本与收益的角度,解读作战理论边际效益原理,以期为洞察未来战争作战指导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乔纳森·利维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时代》一书中,介绍了工业隐藏的秘密——工业创造财富的动力学原理。假设一个钢铁厂前期的固定投资为100万美元,包括厂房、机器、工人等等。如果只生产1吨钢,这吨钢的成本就是100万美元加上1吨钢的原材料;如果生产2吨钢,平均每吨钢的成本就是50万美元加上1吨钢的原材料。以此类推,这个工厂生产的钢越多,平摊到每吨钢上的成本就越低;其成本越低,可以容忍的价格就越低;价格越低,能抢占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市场份额越大,需要的产量就越高;产量越高,其每吨钢的成本就进一步降低……这是一个正反馈良性循环。
当时的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发现了这个秘密。他采取了包括控制流程、降低成本、更新设备、提升效率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加快了这个“财富飞轮”的运转速度。于是,他的公司规模越来越大,产品越来越便宜,利润也越来越多。卡内基本人也被誉为“钢铁大王”。

工业创造财富的动力学原理,其关键就是边际效益递增。在工业之前的几千年农业时代,世界人均GDP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工业后,世界人均GDP大幅增长。为什么?因为农业本质上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产业。比如一亩地,可以雇用一个人耕种;如果安排两个人一起耕种,尽管可以搞精细化作业,但土地的产量并不会因此而翻一番;如果安排三个人耕种,增加的产量大概率会比两个人耕种时增加的更少。随着劳动力的增加,这亩地的产量平均在每个人身上是下降的,这就决定了农业很难规模化。而工业却是一个在一定范围内边际效益递增的产业,所以工业时代的产品和财富均呈指数级增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作战理论的演变过程,与工业发展的动力学原理相似,同样遵循边际效益原理。以基本作战原则“集中兵力”为例:假设组织三次红蓝对抗,蓝方均为100人,红方分别为200人、300人和400人,双方单兵战斗效能均为0.2,那么双方每小时的战损就是“对方剩余兵力与单兵战斗效能的乘积”,当战斗持续时间不足1小时时,按照蓝方剩余兵力被消灭对应的时间计算红方战损。

当蓝军100人、红军200人时:1小时后,蓝方损耗兵力为200×0.2=40人,剩余兵力为100-40=60人;红方损耗兵力为100×0.2=20人,剩余兵力为200-20=180人。2小时后,蓝方损耗兵力为180×0.2=36人,剩余兵力为60-36=24人;红方损耗兵力为60×0.2=12人,剩余兵力为180-12=168人。同理可以得出,3小时内蓝军被全歼,红军战损为36人。以此类推,当蓝军100人、红军300人时,2小时内蓝军被全歼,红军战损为26人;当蓝军100人、红军400人时,2小时内蓝军被全歼,红军战损为22人。
由上面计算过程可知,当蓝军被消灭时,红军初始兵力越多,战损越小。这种计算方式属于概略计算,存在一定误差,使用兰彻斯特方程还可以得出更加精确的结果,但结论是一致的。这一结论充分解释了“集中兵力”的优势:兵力占据优势的一方不仅能够最终赢得胜利,而且兵力优势越大,战斗损耗越小。但是,从边际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看,红军从200人增至300人,减少的战损为36-26=10人;从300人增至400人,减少的战损为26-22=4人。增加相同规模的兵力,能够降低的战损却越来越少。这说明,集中兵力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

集中火力也是一样的道理。火力越强,对方伤亡越大,其对己方的杀伤能力就越弱,那么己方的损耗就越小。根据兰彻斯特方程,这种损耗也呈递减趋势。所以,集中火力也符合边际效益递减原理。事实上,兵力是火力的基本载体,集中兵力与集中火力本质相通,二者都是集中“战斗能量”。
从定义来看,合同作战与联合作战本质相同,其差别在于协同的范围和规模不同。从边际成本与收益的角度来看,二者的边际效益是递增还是递减呢?可以构建一个简单的作战场景进行推导。假设甲、乙两个分队对单位面积内目标的侦察效能分别为R1、R2,打击效能分别为A1、A2,那么甲分队的作战效能可简单视作F1=R1A1,乙分队的作战效能视作F2=R2A2。

当甲、乙各自为战时,情报信息和打击能力没有实现互联互通,其总体作战效能为R1A1+R2A2;当甲、乙协同作战时,情报信息和打击能力实时共享,其总体作战效能为(R1+R2)(A1+A2)。很显然,(R1+R2)(A1+A2)R1A1+R2A2。这说明,协同作战始终比各自为战拥有更高的作战效能。那么,协同作战增加的作战效能是从何而来的呢?
令二者相减,得到R1A2+R2A1,这就是二者相差的战斗效能,也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联合作战“1+12”时所产生的战斗增益。从实际作战的角度来看,这部分增益意味着当甲、乙因客观条件限制,难以打击自身侦察发现的目标时,可以通过情报共享,交由对方来实施打击。即在各自为战的基础上,增加了双方协同作战的效能R1A2和R2A1。
例如,在2020年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爆发的纳卡冲突中,阿塞拜疆TB-2无人机在野外遭遇一支亚美尼亚步兵部队,立刻展开攻击。但是亚美尼亚步兵很有经验,整支部队迅速疏散隐蔽,使无人机难以通过挂载的几颗炸弹实施大规模空袭。阿塞拜疆无人机在发现无法消灭这支部队后,立即将目标坐标信息和视频传输给后方火箭炮部队。于是,在无人机的精确引导和毁伤评估下,阿塞拜疆火箭炮部队在几十公里外进行了精确火力覆盖。最终,亚美尼亚一个整建制步兵营在短期内即被摧毁。在这一战例中,阿塞拜疆无人机和远程火箭炮的协同作战,是其达成作战目标的关键因素。
根据前面的推导过程,如果甲、乙基础上再增加丙分队,其战斗增益会增加“R1A3+R2A3+R3A1+R3A2+R3A3”,很容易证明这个值比“R1A2+R2A1”更大。也就是说,增加第三个分队的战斗增益大于增加第二个分队的战斗增益。这说明无论合同作战还是联合作战,它们的边际效益都是递增的。
如果继续深入进行推导,会发现随着参战力量联合规模的扩大和联合程度的加深,联合作战的战斗增益是呈指数级上升的。这说明“1+1不仅大于2,而且远远大于2”。
综上所述,集中兵力、集中火力与合同作战、联合作战相比,前两者通过增加数量来减少损耗,其边际效益递减;后两者则通过资源共享来提升效能,其边际效益递增。由此可见,在空间拓展、维度增多、武器杀伤力不断增大的现代战场上,需要但不必过于追求兵火力优势,而更应该在建立一定优势的基础上,将所有作战资源接入“杀伤链”,编成“杀伤网”,寻求通过作战资源的共享,提高作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作战行动的一体化。
那么,在智能化战争形态下,会孕育出哪些新的作战理念呢?笔者认为,集中兵火力的本质是通过更多兵火力资源建立能量优势,联合作战的本质是通过作战资源的广域分布和快速共享建立时空优势。智能化战争的发展趋势,将是通过增强信息的流转、交互、处理等能力来建立决策优势,为所有作战单元赋能。这三类优势的关系是:后者是更高维度的优势,可以兼容和转化为前者。即,时空优势可以转化为更高维度的能量优势,决策优势则可以转化为更高维度的时空优势。打个比方,如果说集中兵力是为算法提供充足数据,那么联合作战就是提高算法运行效率,从而提高数据的利用率;而智能化战争则是对算法本身进行优化,从而实现不仅提高运行效率,而且用较少的数据输入就能达到同样甚至更高质量的信息输出。由于信息复制、传递的成本非常低,那么可以预想,智能化战争形态下基于“信息赋能”的作战理论,必然会带来更加显著的边际效益递增。